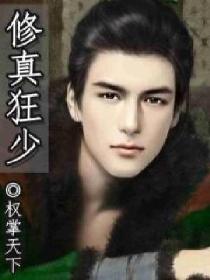松本清张提示您:看后求收藏(吾看中文5kzw.net),接着再看更方便。
1
阁下
之所以只写了“阁下”二字却空着姓名,主要是我至今仍在犹豫该寄给谁。或许会填上警视厅某搜查官的名字,抑或理所当然地填上律师的名字,再不然就这样任其空白。在没写完这封信之前,我还无法作出决定。
况且我还不太确定究竟要写成信还是手记。如果写成信函,行文未免太过复杂,有点失礼;如果当做手记,预设收信人的文体又过于个人化。索性让这篇文章介于这两者之间吧,应该也没什么关系,而且这样更能意有所指。
要写这个,就得从昭和二十五年(一九六〇年)的四月谈起,距今七年。
当时我任职于东京某银行,三十一岁。公司在日本算是一流银行,单身的我对生活状况毫无不满,每天都过得有趣,对未来也和一般人一样抱有希望。
我在阿佐谷车站后面租了一间房子,和妹妹同住。那时那附近有一小片杂木林,不过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。如果勉强嗅闻,多少还能嗅出几分武藏野的天然气息,每天搭车上班的生活对我来说十分愉快。
我妹妹名叫光子,当年二十七岁。她十九岁那年结婚,眼看着战争即将结束时丈夫却战死了,是个不幸的战争未亡人。我只有这么一个妹妹,遂把她接来照顾。幸好她没有孩子,我总是暗自留意,看有没有适合她的对象,想让她再婚。
妹妹天性开朗,总是一边唱歌一边在厨房整理或洗衣服,有时候我嫌吵还会骂她两句。我从银行下班后,只要一走到家附近,总会听到《从上海回来的梨琉》之类的旋律。当时这首歌刚开始流行,妹妹很喜欢。有时候我和也住附近的同事笠冈一起下班回家,听到时还真有点不好意思。
“哪里哪里,开朗活泼是好事呀!”
笠冈说完便看着我笑了,他四十二三岁,不是我的顶头上司,是另一课的课长。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方向,所以经常一起上下班。
“喂,你都这把年纪了,还好意思大声唱歌,别闹了好不好!”
我刚关上格子门,便站在玄关处对妹妹怒吼。光子吐吐舌头。
“哎哟,我真有那么老吗?”她说。
“对呀,女人年近三十就算老太婆了。”
“讨厌!干吗多算人家三岁。你知道吗?还有很多人喊我小姑娘呢!”
光子说得没错,可能是因为身材娇小吧,她看起来的确比实际年龄要小。也许是因为婚姻生活短暂,她的个性还有些幼稚,穿起花哨的洋装倒也很合适。
“说这种话会被人家笑话哦。刚才就是,我和笠冈先生一起回来,走到巷口就听到你那大嗓门,人家都苦笑了呢!”
“哎哟,怎么可能。”妹妹说,“笠冈先生还夸奖过我,说我歌唱得很好听呢。他好亲切啊,他还说第一次看到我时,以为我只有二十岁出头呢。”
“哼,你少得意了。”
我感到很不快。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妹妹,另一方面是对不知不觉竟和我妹妹熟到会说这种话的笠冈有点不悦。有人瞒着自己在背地里做事,多少总会让人不快的吧。
况且,这个笠冈虽已四十出头,却是个浓眉大鼻、看起来精力旺盛的男人,之前就曾听说他多次出轨,让妻子受了不少委屈。看来还是防着点好,一旦发现什么征兆,一定得警告妹妹。
从那时起,我便不动声色地暗中观察,不过一切并无异样。既然毫无问题,我自然也不好再啰嗦什么,反而觉得自己瞎操心,错怪了好人。
又过了几个月,到了六月底。某天光子吃完早餐后对我说:“哥,后天是辉南的忌日,我好久没去扫墓了,想回乡下一趟。”
辉南是光子的亡夫,这里的“乡下”指的是山形。光子的确有两年没回去了。
“也是,好久没问候人家也不好,那你去吧。”
我爽快地答应了。当天还从银行预支了薪水交给光子。
“不用啦,反正我也用不到什么钱。”
光子客气地推辞,但我还是硬塞到她手里。事后回想,或许算是一语成谶吧。
隔天早上,光子神采奕奕地走出家门。可能是很高兴吧,天还没亮她就起床准备,又哼唱起那首《从上海回来的梨琉》。不过,她这次没敢唱得太大声,我也就没骂她。我正好要去上班,便跟她一起走到新宿车站。
“再见。”
她站在月台上,对挤进开往东京的满员电车中的我挥挥手,夏日的朝阳照亮了她的半边脸。
那天,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光子。
2
光子就此失踪了。
我在一个星期之后确定了这一点。我发了一封电报给她在山形的婆家,对方回复说光子根本没来过。我不禁愕然。
为谨慎起见,我又搭快车去了一趟山形。她的确没来过,对方也是一脸忧虑。我们商量之后决定我马上回东京去警视厅报案。我把她的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离家当天的穿着等详细特征,附上一张近照一并交给警方。脑海中不停浮现不祥的景象,不安与恐惧令我夜夜无法入眠。对于报警寻人,我一半期待一半其实已死心,警方正忙着处理更重大的案件,我不认为他们会认真到为了这种小事费神。
对于光子离家的原因,我毫无头绪,之前也看不出任何迹象。如果她真的失踪了,那绝非出于自愿,一定是遭人挟持。我很后悔为何让她一个女孩子单独出远门。可话说回来,她都二十七岁了,不需我随伺在侧。不过如今回想起来,没陪她一起去似乎是个严重的错误,我非常后悔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,我只能作最坏的打算。我急忙订了三份报纸,每天搜寻社会版,心里虽然害怕,却还是强迫自己去看。
大约在光子离家后的第四天吧,早晨上班途中我遇见了好几天没碰面的笠冈。
“这阵子令妹不在吗?我看你家的门总是锁着。”他问。
“对,她去乡下了。”
“哦,哪里的乡下?”
“山形。”